晚唐文人的特殊嗜好:在青楼妓女大腿上作诗题词
字号:小号|大号
推荐阅读
一头水牛单挑7头狮子 结局一幕让人瞠目结舌 更新时间:18:00:37
更新时间:18:00:37
沙滩情侣不雅行为 光天化日现场“直播” 更新时间:11:48:51
更新时间:11:48:51
深航空姐刘瑞琦艳照门视频曝光 自摸私处画面淫荡不堪 更新时间:16:52:38
更新时间:16:52:38
本周热门
- 南明弘光帝有多荒淫:当众将幼女演员强奸致死
- 揭秘:历史上刘邦为何对老实厚道的大哥耿耿于怀
- 惊:史上竟然有吃美女的习俗
- 梁山好汉五大好色之徒:宋江竟榜上有名
- 宋朝是bet365365体育上最繁华 百姓最幸福的朝代吗?
- 司马懿之妻张春华为何亲手杀人!司马懿老婆是谁
- 古龙笔下最精彩的15部小说及十大枭雄介绍
【内容导读】到了晚唐以后,诗文里的青楼更多了一些生活气息,艳浮之作不少。被诗化的不仅是妓女的精神,连妓女的身体也包括了。如有一首诗写的是在妓女大腿上题词之事:慈恩塔下亲…
到了晚唐以后,诗文里的青楼更多了一些生活气息,艳浮之作不少。被诗化的不仅是妓女的精神,连妓女的身体也包括了。如有一首诗写的是在妓女大腿上题词之事:
慈恩塔下亲泥壁,滑腻光滑玉不如。
何事博陵崔四十,金陵腿上逞欧书。
据说外国有些姑娘也喜欢请作家在她们的玉腿乃至酥胸上签名题字,肯定是从这位中国唐妓处学去的。
唐代还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叫《游仙窟》。所谓的仙窟即是青楼。一是人们喜欢诗化自己的风流艳事,二是青楼之游也的确令人欲仙欲死。所以古人道“游仙”时,常常就是嫖妓,就像西方人说去洗手,实际上是去撒尿一样。
《游仙窟》用极长的篇幅详细叙述了主人公如何来到仙窟,受到了如何盛情体贴的款待,并调动各种修辞手段描写主人公与两位妓女互相戏谑、挑逗,写得极为生动活泼,才华横溢,艳而不俗,色而不淫。即使是肉体交欢的段落,也极力诗化之,最后临别时无限伤感,发出“人生聚散,知复如何”的慨叹。其实青楼之欢,不就是“为了告别的聚会”吗?
整个唐代文学中的青楼,都给人一种仙境之感。仿佛是“青楼只应天上有,人间能得几回游?”

到了宋朝,词这种文学形式发展得铺天盖地,以至搞得许多后人只知有宋词而不知有宋诗了。其实,宋词与青楼的关系比唐诗还要亲密。去掉青楼,唐诗的损失并不太大,只是结构性的,不是总体上的。而宋词若是离了青楼,简直就溃不成军,只剩下几个“豪放派”的傻老爷们,手持铜琶铁板,干吼着“大江东去”,知道的是唱宋词,不知道的还以为要表演硬气功呢。
随便翻翻宋人的词集,诗化青楼之作俯拾皆是,故这里不作抄录。一般说来,“诗庄词媚”,词这种形式,特别适合吟风弄月,传情表爱。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,除了热恋就是失恋。所以,比之于诗,词更加真实、更加细致地写出了妓女和客人们曲折微妙的心理情感。但也正是于此,理想的色彩减少了,仙境的感觉冲淡了,给人更突出的印象是一种人生雅趣。像柳永的“忍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唱”,多么潇洒适意。秦观的“此去何时见也,襟袖上空惹啼痕”,多么地一往情深。周邦彦的“琵琶轻放,语声低颤,灭烛来相就”,多么地温香醉人。较之唐诗,许多人更爱宋词,原因恐怕就在于宋词更好地表达了人之常情吧。宋词把青楼诗化得温馨可人,当真宛如十七八女郎,执红牙板,歌“杨柳岸晓风残月”,我见犹怜,能不叫人爱煞乎?
到了元朝,作家们都成了臭老九,地位与妓女不相上下,所以诗化青楼之作表现出两种倾向:一种是把青楼写成淫冶放荡之所,借以抚慰或发泄自己不平衡的心情;另一种是反映青楼黑暗面,写妓女的不幸和反抗,从中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。大戏剧家关汉卿就塑造了赵盼儿、宋引章、谢天香、杜蕊娘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妓女形象。这时的青楼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个战场,需要斗智斗勇。当然,结局总是大团圆的。中国人在最悲惨的情况下,也不会放弃对这种诗化模式的偏好。所以,青楼仍然是美的。
明朝据说是资本主义萌芽了,于是青楼里涌进来许多暴发户的款爷,左一张港币,右一张美钞,你想钱那东西是天底下最脏的,这么一来,无论怎么诗化,青楼都多少有点洗不干净了。像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中的花魁娘子莘瑶琴还是懂得人间真情,蛮可爱的;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中的杜十娘更是光彩照人,比我们这些俗人要干净一万倍。但是像《金瓶梅》等作品中所写的那些李桂姐、吴银儿、郑爱月等人,却实在是青楼里的败类。此外,青楼里又多了许多“棒尖”的帮闲无赖王八蛋,欺内瞒外,乌烟瘴气。如此一折腾,青楼的形象遭到了破坏。也许这属于一种“现实主义”诗化吧,不能让青楼总那么“月朦胧,鸟朦胧”下去,是骡子是马,该拉到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去遛遛了。
到了清朝,除了有《桃花扇》这样的“借离合之情,写兴亡之感”的历史剧继续美化李香君这样的侠烈妓女外,出现了大量的狭邪笔记和小说。在这样的文字中,青楼像家常便饭一样被谈论、被调侃,悲剧、喜剧都变成了闹剧。直到20世纪初,《九尾龟》、《海上繁花梦》等书刊行后,青楼已然诗味寡然。随着青楼的衰落,人们越来越不会做梦。聪明的人们着穿了仙境的不实,看穿了雅趣的无用,他们抛弃了酸文假醋的诗化,直截了当地说着“嫖娼”或“逛窑子”或“打野鸡”。历史的车轮在前进,辗碎了青楼之梦、红楼之梦。会作诗填词、会琴棋书画的青楼女子没有了。只有一些天天关心自己三围的靓女们,游荡在人生的舞场边,在等待西门庆的金牙一闪,便好“与狼共舞”。
没有诗化的青楼,不论设备多么现代化,服务多么专业化,都等于猪圈!
慈恩塔下亲泥壁,滑腻光滑玉不如。
何事博陵崔四十,金陵腿上逞欧书。
据说外国有些姑娘也喜欢请作家在她们的玉腿乃至酥胸上签名题字,肯定是从这位中国唐妓处学去的。
唐代还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叫《游仙窟》。所谓的仙窟即是青楼。一是人们喜欢诗化自己的风流艳事,二是青楼之游也的确令人欲仙欲死。所以古人道“游仙”时,常常就是嫖妓,就像西方人说去洗手,实际上是去撒尿一样。
《游仙窟》用极长的篇幅详细叙述了主人公如何来到仙窟,受到了如何盛情体贴的款待,并调动各种修辞手段描写主人公与两位妓女互相戏谑、挑逗,写得极为生动活泼,才华横溢,艳而不俗,色而不淫。即使是肉体交欢的段落,也极力诗化之,最后临别时无限伤感,发出“人生聚散,知复如何”的慨叹。其实青楼之欢,不就是“为了告别的聚会”吗?
整个唐代文学中的青楼,都给人一种仙境之感。仿佛是“青楼只应天上有,人间能得几回游?”

到了宋朝,词这种文学形式发展得铺天盖地,以至搞得许多后人只知有宋词而不知有宋诗了。其实,宋词与青楼的关系比唐诗还要亲密。去掉青楼,唐诗的损失并不太大,只是结构性的,不是总体上的。而宋词若是离了青楼,简直就溃不成军,只剩下几个“豪放派”的傻老爷们,手持铜琶铁板,干吼着“大江东去”,知道的是唱宋词,不知道的还以为要表演硬气功呢。
随便翻翻宋人的词集,诗化青楼之作俯拾皆是,故这里不作抄录。一般说来,“诗庄词媚”,词这种形式,特别适合吟风弄月,传情表爱。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,除了热恋就是失恋。所以,比之于诗,词更加真实、更加细致地写出了妓女和客人们曲折微妙的心理情感。但也正是于此,理想的色彩减少了,仙境的感觉冲淡了,给人更突出的印象是一种人生雅趣。像柳永的“忍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唱”,多么潇洒适意。秦观的“此去何时见也,襟袖上空惹啼痕”,多么地一往情深。周邦彦的“琵琶轻放,语声低颤,灭烛来相就”,多么地温香醉人。较之唐诗,许多人更爱宋词,原因恐怕就在于宋词更好地表达了人之常情吧。宋词把青楼诗化得温馨可人,当真宛如十七八女郎,执红牙板,歌“杨柳岸晓风残月”,我见犹怜,能不叫人爱煞乎?
到了元朝,作家们都成了臭老九,地位与妓女不相上下,所以诗化青楼之作表现出两种倾向:一种是把青楼写成淫冶放荡之所,借以抚慰或发泄自己不平衡的心情;另一种是反映青楼黑暗面,写妓女的不幸和反抗,从中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。大戏剧家关汉卿就塑造了赵盼儿、宋引章、谢天香、杜蕊娘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妓女形象。这时的青楼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个战场,需要斗智斗勇。当然,结局总是大团圆的。中国人在最悲惨的情况下,也不会放弃对这种诗化模式的偏好。所以,青楼仍然是美的。
明朝据说是资本主义萌芽了,于是青楼里涌进来许多暴发户的款爷,左一张港币,右一张美钞,你想钱那东西是天底下最脏的,这么一来,无论怎么诗化,青楼都多少有点洗不干净了。像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中的花魁娘子莘瑶琴还是懂得人间真情,蛮可爱的;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中的杜十娘更是光彩照人,比我们这些俗人要干净一万倍。但是像《金瓶梅》等作品中所写的那些李桂姐、吴银儿、郑爱月等人,却实在是青楼里的败类。此外,青楼里又多了许多“棒尖”的帮闲无赖王八蛋,欺内瞒外,乌烟瘴气。如此一折腾,青楼的形象遭到了破坏。也许这属于一种“现实主义”诗化吧,不能让青楼总那么“月朦胧,鸟朦胧”下去,是骡子是马,该拉到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去遛遛了。
到了清朝,除了有《桃花扇》这样的“借离合之情,写兴亡之感”的历史剧继续美化李香君这样的侠烈妓女外,出现了大量的狭邪笔记和小说。在这样的文字中,青楼像家常便饭一样被谈论、被调侃,悲剧、喜剧都变成了闹剧。直到20世纪初,《九尾龟》、《海上繁花梦》等书刊行后,青楼已然诗味寡然。随着青楼的衰落,人们越来越不会做梦。聪明的人们着穿了仙境的不实,看穿了雅趣的无用,他们抛弃了酸文假醋的诗化,直截了当地说着“嫖娼”或“逛窑子”或“打野鸡”。历史的车轮在前进,辗碎了青楼之梦、红楼之梦。会作诗填词、会琴棋书画的青楼女子没有了。只有一些天天关心自己三围的靓女们,游荡在人生的舞场边,在等待西门庆的金牙一闪,便好“与狼共舞”。
没有诗化的青楼,不论设备多么现代化,服务多么专业化,都等于猪圈!
历史解密战史风云野史秘闻风云人物文史百科
左良玉在明末为什么能手握百万雄兵?
左良玉是明朝将领,多次与农民起义军征战,到了后来他拥兵百万,成为南明朝廷最重要的倚仗。这位将领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,对于他...详情>>
看亚美尼亚特种兵如何玩命:生食兔肉脚上点火!
亚美尼亚特种兵在武装部队情报局成立纪念仪式上,表演生吃活兔、头顶碎大石、刀扎肚皮、脚上点火……精彩与彪悍程度令人乍舌。相...详情>>
水浒传里花和尚鲁智深为什么说他最后成了佛?
征方腊会老,梁山众将十去七八,战死者、病死者不在少数,那么作为梁山108将中,最为光彩照人的好汉鲁智深,他的归宿在何处呢?为...详情>>
王安石严于律己:从未包二奶 一生无任何绯闻
北宋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,文官的地位很高。在当时的京城开封,许多国家公务员追求享乐和奢侈的生活,娶小老婆和包“二奶”的国...详情>>
吴禄贞一生是怎样的?吴禄贞一生都做过哪些事?
吴禄贞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,家有薄田10亩,父亲为私塾老师。少年时,吴禄贞就读于父亲在武昌的梦泽书屋,他擅长诗文,对西学充...详情>>
 惊吓!响尾蛇有多恐怖?死后一小时内还能袭击人
惊吓!响尾蛇有多恐怖?死后一小时内还能袭击人 丈夫发现妻子同时与7男暧昧 他竟这样做……
丈夫发现妻子同时与7男暧昧 他竟这样做……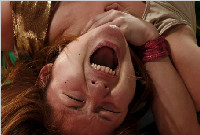 岛国女子摔跤,另类女优演绎暴力性感
岛国女子摔跤,另类女优演绎暴力性感 图揭神秘职业者:一名女入殓师的日常
图揭神秘职业者:一名女入殓师的日常 男优忆初入AV界报酬:为15000日元吃大便
男优忆初入AV界报酬:为15000日元吃大便 热舞太激烈?辣妹下体突然喷火自燃 让人看傻眼
热舞太激烈?辣妹下体突然喷火自燃 让人看傻眼 落单野牛被群狮围攻 整个过程惨烈至极
落单野牛被群狮围攻 整个过程惨烈至极 豹子将疣猪的肚子咬穿,本以为已经死了的疣猪在最后做出了这种事
豹子将疣猪的肚子咬穿,本以为已经死了的疣猪在最后做出了这种事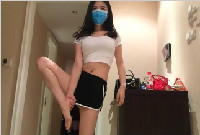 网络女主播直播“练体操” 开腿姿势太犯规
网络女主播直播“练体操” 开腿姿势太犯规 实拍狮子捕食野牛后脑袋卡入肛门 被活活憋死
实拍狮子捕食野牛后脑袋卡入肛门 被活活憋死 “夜间摄影之鼻祖”布拉塞名作
“夜间摄影之鼻祖”布拉塞名作 漂亮的以色列女兵训练起来很凶悍!
漂亮的以色列女兵训练起来很凶悍! 布什总统与伤兵
布什总统与伤兵 拍卖会上的中国文革时期影像
拍卖会上的中国文革时期影像 百年前的欧洲妓女秘照
百年前的欧洲妓女秘照 老照片:据说是为了炫耀弹力丝袜
老照片:据说是为了炫耀弹力丝袜 德军当街屠杀无辜市民
德军当街屠杀无辜市民 六年前北京申奥成功!
六年前北京申奥成功! 胡同里的站街女孩儿
胡同里的站街女孩儿 民生写真:我也有手机了
民生写真:我也有手机了